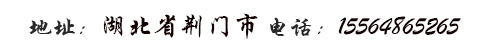郁金香庭院的聚会谢冕
|
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pf/a_4438675.html 丹曾文化特别为谢冕先生开设专栏,将他充满诗意的生活态度向大众传递。本文选自谢冕先生的《博雅文章采薇辞》一书。 谢冕先生的《博雅文章采薇辞》 郁金香庭院的聚会 文/谢冕 郑敏先生的家很有韵味,院里的郁金香开得茂盛,还有书房里飘出的悠扬的琴声,那是北京西郊清华园一道诱人的风景。那时我住畅春园,郑敏住清华园,北大和清华只有一墙之隔,我们两家是很近的。80年代初期,诗人们从蒙难中归来,九叶中凋落了穆旦,引人叹惋,所幸其余八叶都还健旺,充满生命力的绿色在早春的阳光下蓬勃着。辛笛、唐湜、唐祈、曹辛之、杜运燮、袁可嘉、陈敬容,还有郑敏。陈敬容先生鬓见偶见灰白,而郑先生依然青丝如黛。他们劫后重逢,自有难言的喜悦。郑敏(左)谢冕(右) 他们很珍惜这美好的时光。有时辛笛或唐湜从南边来,有时唐祈从西边来,他们总找时间聚会。那时不时兴酒店会面,郑敏先生家院落清雅也宽敞,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那时出租车还不多,而且对于诗人而言还有点奢侈。这些从南边或西边飘来的绿叶,多半会采取公交出行。坐公交车去清华园,我的畅春园住所往往就是这些远道跋涉的诗人们的中途打尖儿的“中间站”。有时,某片叶子坐了一阵,继续自行飘走了,有时我会陪他们一道前往清华园,参加他们八叶或几叶的聚会。就这样,我就熟悉了郑先生的家。九叶都是我的前辈,我对现代诗的热情是受到他们的引领的。他们的作品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异的天空。一本用平日攒下的所有零花钱换来的《手掌集》,伴随我走过长达六十余年的人生。郑敏先生的诗,则是我在中国台湾做新闻工作的二哥远道寄来的剪报,被我珍宝般收藏的。而我的批评文章的风格是学唐湜先生的。八叶都是我的心仪已久的老师,但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他们的朋友,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我不只一次参加过郑先生的家宴。来宾以九叶成员为核心,有时也有像我这样的他们的朋友,但多数属于来自学院的学者。这些家宴多半是西式的冷餐会,有时也会自家做几样中式的热菜。一些冷饮,一些红酒,一些茶,一杯咖啡,人是散落地坐着,边吃边谈,有时也读诗。有时童蔚也来坐坐,童诗白老师多半不参加谈话,他会在自己的书房用琴声来为诗人们助兴。每次参加郑先生庭院的冷餐会,那种氛围总让我联想起当年林徽因先生的客厅的聚会。同是女诗人,林先生那里也许更浪漫,郑先生这里也许更学术。前者似乎更无拘束,后者则更有一些学术气氛和沧桑感。郑敏先生的家是诗意的、让人温馨的。花香、琴韵、优雅的谈吐,这些让我们感陌生而又亲切的,与我们久违了的情调的重现,最生动地说明着九叶诗人的教养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他们是有着深厚的中国学养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来自解放区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久为动乱所苦的人们,九叶的重现,以及它们的受到尊重,象征着中国文化的转机。这种离乱之后的聚会的喜悦,意味着失而复得的欢喜,这欢喜不仅属于他们,而且属于中国。多么令人怀念的80年代!年6月30日于北京昌平(作者:谢冕) [作者简介] 谢冕 福建福州人,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新诗总论》总主编、《诗探索》杂志主编。出版有诗歌、散文及学术专著六十余种。他的理论批评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关怀基础之上,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视点,倡导建设性的理论批评立场。谢冕教授一直站在当代诗歌评论前沿,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ujinxianga.com/yjxwh/5877.html
- 上一篇文章: 肝癌中医辩证论治第二千六百二十二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