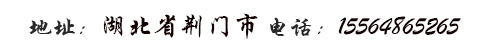谢谢你偶然或刻意瞥见,这本花了我二十四年
|
甲氧补骨脂素能否治好白癜风 http://baidianfeng.39.net/a_yufang/140118/4329295.html ? ▲那年我甫从大都会壮美的艺术品中离开,于走下博物馆的阶梯时遇见美:一个吹笛人正在迷惑两个孩子。(吴明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年) 初拿到吴明益老师谈摄影的《浮光》一书,惊艳于封面的好看和不可思议的绒面触感,终于断断续续读完,觉得文字之美已然超过外在的精致。 大陆知名摄影师严明(著有《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这样写道:“用一个下午仔仔细细看完这本书,并少有地在书上画了很多很多横线,一切因为所言极是。他说,摄影人终其一生都在追猎光的标本,面对照片追忆重温那曾亲临的现场,然后他们将会发现,自己才是光与相机所捕捉的。” 摘选《浮光》是一次漫长的过程,因为文字太过流畅而一气呵成,每每因篇幅限制“掐”掉中间的部分文字时,都有一种割裂的感觉,以致一直拖到现在才呈现。 这是一个文学系教授的私人摄影史,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对摄影与生活的思考。 ●●● 浮光 文 吴明益 我把这些文章分为“正片”和“负片” 值得拿到阳光下检视的 以及放在防潮箱里不轻易示人的 我的镜,我的窗 我的火,我的光 对我来说,将影像化为文字, 也等于在寻找希望。 谢谢你偶然或刻意瞥见, 这本从第一张影像开始 花了我二十四年的书 吴明益光与相机所捕捉的HuntingWildLifwithCamraandFlashlight 我将用我的余生来思索,光是何物。 爱因斯坦正片摄影者开始发现自然界的诗意后便停不下来,毕竟捕捉动物一瞬间运动状态的不只是机械,还是心灵。美的唤醒如此独特,以至于同样一台机械交给不同的人将获致不同的结果,而同样一张照片带给观看者的情绪震动,也绝对不是那些一开始希望相机为科学理性服务的人所能理解的。 我最喜爱的一张是三头受到闪光惊吓的鹿,它们瞬间往三个方向分别逃离,因而跳跃停留在空中,健壮的后腿诗意弥漫,美在夜色中被发现。 ▲夏伊拉斯三世作品,收录于《以光与相机所捕捉的野生动物》, 随着相机愈来愈轻便,快门愈来愈迅速,相机渐渐和过去的猎枪一样,成为博物学者行走野地必然携带的工具。苏珊·桑塔格认为拍照和战争、迁徙行为有可以类比之处。 每个野地摄影家的装备里,都有火药的雏形,他们警觉周遭的草动风吹,他们用光和相机捕捉陌生的野地与陌生的生物,仿佛在进行着一种“杀伐旅”[Safari]。 我想起摄影家阿道夫·布朗那幅称为《鹿和野禽》[DrandWildfowl]的照片,画面里有一头鹿、一只绿头鸭、一只雉鸡,以及另一只难以辨识的水禽。这些已然丧失生命的生物,和杀害它们的猎枪、编织袋与铜管喇叭吊在一起,鹿的头垂到地上,前肢呈跪姿—整幅照片就像他向来喜爱拍摄的花艺盆栽似的。 ▲阿道夫·布朗作品《鹿和野禽》,年 但自然不是盆栽,拿着猎枪和拿着相机记录下这个“静物画面”的可能都是阿道夫·布朗,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想象使得这张照片对我而言,呈现了人所可能决定如何对待自然的双面性:可以用火药可以用光。 负片1 一九九四年的某天,当悍马车绕过村子,经过空军官校旁时,我在车的后座看到了可能成为一张照片的影像。几乎没有迟疑,我拍了拍驾驶兵的窗户,问他可不可以停下来等一会儿。我跳下车,按下快门,再跳上车。那是一只死去的两腿僵直的鸡,翅膀微微打开躺在马路上。透过观景窗,可以看见鸡的眼窝微微下陷。完全是机遇的安排,那死鸡的旁边,恰好有一个印着裸女的空槟榔盒。它就在那里。 ▲吴明益,冈山空军官校旁,年 虽然很多拍生态摄影的人宣称他们爱自然、爱动物,但我知道那样的爱跟一般我们称为爱情的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唯一相同的是,可能都有根本的脆弱性。 多年以后,我再看到那张照片里的死鸡时,想到自己当时或许被某种神秘主义、陌生化或机遇之类的构图所吸引而按下快门。云挡住了阳光,影子不在了,某一刻此身将会被称为尸体,而不再被称为肉体。但我也同时明白了自己拍下那张照片时,对那只死去的鸡是几乎不带感情的,那是一张或许有意味,对我来说却缺乏情感有效性的照片。 2 在吴哥窟每一个观光景点,你都会看到年纪非常小的孩子使用中文向华人面孔的游客兜售明信片、T恤或书。他们也会在你进入某个庙宇前偷偷拍下你的照片,然后立刻用一旁小店里的打印机印下来,贴在粗糙的瓷器上卖给你。他们会像小动物一样紧盯着你直到完全绝望,那一刻祈求的眼神立刻转变成空洞,那些孩子会毫不犹豫把你的照片撕下来丢到垃圾筒,准备贴上另一个游客的照片。 半生投入奴隶救援工作的亚伦·科恩揭露了柬埔寨可能是此刻世界上存在着最多童妓的国度。童妓的来源除了当地以外,也有从越南、缅甸而来的孩子,年纪通常在八岁到十四岁之间。科恩为取得犯罪资料,多次亲身进入妓院涉险,拍下足以作为证据的照片。他不得不与这些眼睛异常美丽族群的孩子眼神接触,但总在回到旅馆时呕吐,想起自己或许看到的是《约伯记》里的“死亡的大门、阴间的门户”。他说:“如果我可以让一个小孩陈述她的梦想,我就能知道人口贩子还没有完全毁坏她的灵魂。”他一生都在试着拯救灵魂还没有完全毁坏的孩子。 ▲吴明益,柬埔寨达松将军庙,年 在达松将军庙向我兜售明信片和T恤的女孩并不是雏妓,她可能只是跟我小时候一样,为帮忙家计而提早“出社会”而已。或许只是我读过那些报道所引发的多余反应,但我在她的眼里确实看到不可思议的成熟与衰老,也仿佛看到了其他的什么,我一直还不能解释的事。因而纵然她表明愿意让我拍照,但一件T恤换得这张照片,仍带给我一种莫名的歉疚之感。她知道观光客喜欢拍他们的照片,她得答应T恤才卖得出去,而我也知道这一点,这或许是关键。当我在观景窗里接触到她的眼神时,我就知道这张照片必然会是对我有效的,它会跟随我到失去视力的那一天。 稍纵即逝的现象EphmralPhnomna“我们曾经按下的快门,就像放了数十年后的印书纸一样纤薄易碎,是我们追问或想象照片背后的故事让它有了骨骼。它挽救、停留、无能为力却又像是阻挡了稍纵即逝的什么。” 正片照片里的活物,此刻或有一天都将成“逝者”。苏珊·桑塔格说:自从一八三九年照相机发明以来,照片就与死亡相伴而行。 美国第一个大规模拍摄印第安人的摄影师,印第安名为“美丽孤峰”[PazolaWashtPrttyButt]的爱德华·柯蒂斯,从一八九六年开始带着他十四乘十七英寸的沉重相机踏遍美国西部与加拿大的部落。他使用玻璃版独立拍摄了数万张照片,耗去三十多年的青春、体力和金钱,完成二十卷巨著《北美的印第安人》[ThNorthAmricanIndian]。 在他的照片里,一开始阿帕奇人、纳瓦霍人和因纽特人,都仍然穿着传统服饰,生活在野地中,焕发出一种自尊自傲的神采。但到了一九二七年,一位科曼切人的酋长—威尔伯·佩波[WilburPbo],在照片里穿上衬衫打起领带,于是我们发现,照片中不只看到个人的消亡,也看到了族群的消亡、文化的消亡。 ▲爱德华·柯蒂斯作品AnOasisinthBadlands,SouthDakota,收录于《北美的印第安人》,年。?thCharlsDringMcCormickLibraryofSpcialCollctions,NorthwstrnUnivrsityLibrary 柯蒂斯为完成这项摄影的民族志以致穷困潦倒直至去世,但他的精神意识可不穷困。他不但为世人见证了美洲大陆最剽悍族群的余晖,还见证了北美最大有蹄类美洲野牛群仍奔驰在草原上的一刻。 负片还记得高中时要把底片拿到相馆冲洗,大概得等上两天。那两天总让人心焦,在那卷胶卷里的朋友或亲人常会对摄影者询问:“照片洗出来了没?” “还没。” 于是彼此又静静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等待,在照片冲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某张照片拍得如何,有没有晃动到,拍照时是否闭上眼睛。但担任摄影的人隐隐会有印象,因为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观景窗里的形象暂时性地收到脑海里。他吃饭的时候想,那张照片拍得好不好呢?走路时想,我有没有抓住女孩微笑的瞬间?有没有抓住那个老人疲惫的眼神?有没有抓住雨、雾、烟、云?直到睡觉前还在想。不过记忆还是就那么淡去了,就在快要完全忘记的第三天,相片终于真的“被看见”了,时光重返,迷路的孩童发现家正在前方。 斯蒂格里茨吸引我的就是那种时光重现,某种物事却一逝不返的气味。 斯蒂格里茨早期有一张像是在日常家居客厅一角所拍的女子照片,画面里一名女子面对窗户独坐在小圆桌前,墙上贴了几张照片,挂了一个鸟笼和三张像是心形的卡片。墙上照片中包括一名男士和两张一模一样的风景照。小圆桌上放了一张装了框的,可能是女子自己的照片,也和墙上的某张照片重复。壁纸和桌巾的花色乍看非常相近,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不同。窗户向内打开,外百叶窗转到某个倾斜的角度,因此光栅洒了进来,此刻女子正在写些什么,我当她在写信,因为她的神情像在写信。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作品SunRays,PaulaBrlin,年 这是一张小说式的照片。斯蒂格里茨的照片里有音乐,看着看着就出现像风中的郁金香枝那样纤细的乐句,也有像普鲁斯特的小说一样,河流式的情绪与迷人的小细节。从窗户走进来的光线,主人公正在写信的情境,如此像维米尔描绘日常的画作。 彼时只有半天假的午后,我走在村子里正拍着什么,隐隐觉得背后有什么在看着我,回头一看是一只刚刚还没有出现,此刻却坐在公共洗衣台上的猫。我几乎完全没有重设光圈和快门速度,只是反射性地举起相机按下快门。猫在相机咔嚓一声的刹那间,就跳下洗衣台逃走了。 ▲吴明益,弥陀二高村,年 这张照片对我而言不是猫,也不是洗衣台,或是一个老旧眷村的死去,而是光从右上方的屋檐斜斜走进,一进一进的门墙重复却又不重复的意象。那光带着一种一逝不返的气味,带着故事性,它彰显细节、光辉细节。 当你无目的地漫步街道、林道,也许是一只猫,一朵云,一个窗景,一个雨季的肇始,或是一个女人与你擦身而去后随即转过街角。然而她旋即消失,并且永远地离开你。你在那片刻似乎感觉到什么,那种差点就可以摸到的,雾霭一般的事物,悄然渗入身体,你要按下快门,你得按下快门。那张照片将是一份感情,是光阴片刻。于是你肉身的某处被开启,成为一个湖,一个可以让情感片刻栖身的地方。 对场所的回应InRsponstoPlac正片一九四一年,亚当斯为新墨西哥州“美国碳酸钾公司”拍广告而到西南部去,当他驾着车开过一段路时,看到东方月亮升起,挂在云层和积雪围绕的山峰上,另一边则是傍晚的夕阳,半显半隐于朝南流动的云层间。夕阳的微量日光,则恰好映照在教堂墓园的十字架上。他预感到这会是一张他人生里重要的照片,赶紧跳下车,却一时找不到惯常使用的韦斯顿测光表,他突然想起月亮的亮度是每平方英尺两百五十烛光,就依这个数据判断曝光时间与光圈。 手指兴奋得发抖的亚当斯拍了一张,把底片匣翻转过来再拍一张,此时夕阳已离开十字架,神秘的一刻一逝不返了。彼时他并不知道《月升之时,赫南德兹,新墨西哥州》[Moonris,Hrnandz,NwMxico]将会成为他摄影生涯中最知名的照片。 ▲安塞尔·亚当斯作品《月升之时,赫南德兹,新墨西哥州》,年 “二战”期间及其后,正是纪实摄影当道的时代,批评亚当斯没有拍出“那个时代”、不关怀世道的人,常说他“在崩裂的世界中,居然还在拍石头”。亚当斯反驳说自己并非不关心世界与未来,只是不想去重复其他人已经在做的事。他持续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ujinxianga.com/yjxyy/6668.html
- 上一篇文章: 话题如何区分孩子眼睛的近视与弱视
- 下一篇文章: 厉害了武汉居然有一趟吃货专线车吃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