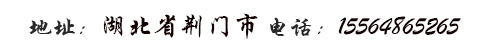好一朵美丽的郁金香
|
沈阳白癜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zyyq/160213/4769999.html 四月,兴庆宫公园的郁金香开得如火如荼。 郁金香看的是规模,红艳艳一大片,金灿灿一大片,白生生一大片,粉嘟嘟一大片……各色花儿齐刷刷站在自家的方阵里,严格听从同一基因指挥,颜色形状高矮一样,每一朵花都贡献一点色块,以期齐心协力震撼眼睛。方阵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暗戳戳的吸睛较量。 郁金香的美还在于单纯,一株一花,谁不挨谁,腰杆笔直,显得独立孤傲。每一株花下面都围着五六片叶子,宽宽的,流线型。叶子们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绝不和花争风头,只一根蒜薹似的细颈将花高高举起,让它端坐在自己的头顶上。所以搭眼望去,上面一层花海,下面一层绿叶海。郁金香有一种纯真即是艳丽的效果。 郁金香造型简洁,内三片外三片共六片花瓣,勺子状,有圆弧形轮廓。花瓣们微微向内收拢,好像外面的大花瓣要去呵护里面的小花瓣,又像正聚在一起说悄悄话。或者像花心里藏了一颗磁石在吸引着它们,反正有一种朝内的凝聚力。花瓣厚实爽利,显得拙稚硬朗,像个帅帅的男孩子,没有它的邻居牡丹身上的娇媚温软。它无细节也无香味,好像在说,我嘛,这样子就够了。事实上单朵的花不到拳头大,显得单薄,所以要成千上万,才有震撼效果。特别是青春期的郁金香们宛如一盏盏彩色玻璃高脚杯,被密密麻麻地放在地上,就好像老天爷要庆祝什么,而摆在人间的酒宴,当然酒杯里有时是满满的琥珀色阳光。 兴庆宫公园里的郁金香有好多品种,一路逛过去,一个方阵接一个方阵,眼花缭乱,有阅兵的感觉。比如“唐吉诃德”,像喝醉了的少女脸蛋,粉嫩粉嫩的,一点都不唐吉诃德;叫“滑雪板”的倒更像皑皑雪野;“帝王血”非常名副其实;“巨粉”有点夸张,它上粉下白,模样更像荷花;“白日梦”黄澄澄,炫如富贵梦,但做得早也醒得早,到四月中旬已消失不见;“金炫耀”的确值得炫耀;“主妇”是恬淡的粉色,像个安静少妇;“阿普多美精英”不知名字啥意思,但它的叛逆看得见,离正统郁金香相去甚远,玫红的花瓣上镶着金边或白边,花瓣尖利,大概因为花到老年,散漫成了水果盘模样;“门特”外面淡粉里面橙黄,像把衣服穿反了的马大哈。 最另类的非“夜皇后”莫属,花如其名,紫黑色,有点像黑布林李子。花型偏小,拘谨地抱成一团,显得冷漠阴郁,甚至邪恶。视线触上去,黑黢黢的,并不悦目,和左邻右舍的灿烂热烈格格不入。但作为花,明艳起来轻而易举,大自然最不会制作的植物颜色恰是黑色。故物以稀为贵,它在郁金香家族中声名显赫,大仲马还写了一本小说《黑色郁金香》,故事是17世纪的荷兰关于培育第一株黑色郁金香的竞争,争斗激起的贪婪和阴谋毁掉了三个人的性命。“夜皇后”这个当年的王谢堂前燕,如今也落入寻常百姓家了。其实每个貌似简单的事物后面都有不简单的故事。 兜兜转转看各色郁金香,会想到诗句:“愿麦子与麦子长在一起,愿河流与河流流归一处。” 据迈克尔·波伦的《植物的欲望》一书记载,郁金香最初的老家在土耳其,当时主要是红色。后来被一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派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带回维也纳,再被一个园丁偷到荷兰,最终在荷兰翻江倒海,名声大噪。据说郁金香首次到欧洲的时候,人们在它身上寻找实用性,有人把它的鳞茎煮熟,加上糖,宣称它是一种美味。有人用油和醋来烹饪它,药剂师把它作为治疗肠胃胀气的药。对此,作家扎比格尼·赫伯特认为:“对于大自然的诗来说,庸俗的功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而迈克尔·波伦说:“郁金香就是美之事物,既不比这多,也不比这少。” 虽然郁金香看似严格遵守自家族群的色彩规矩,但事实上它极易挣脱自己身上基因的控制,喜欢自作主张变色和变形。可能正因为如此,如今才有了如此多的花色品种。即便都是黄色,也有层次丰富的深黄浅黄暖色冷色不同色系,这背后不知道是多少植物学家花了多少心血的结果。一方面同一个阵营里花色严格统一,毫无个性,保证了高纯度,一方面放眼望去五颜六色,还挺矛盾有趣的。 郁金香到了晚期,拉拽它的那股内聚力慢慢涣散变弱了,花瓣渐渐向后仰去,不分内外,花形也凌乱失序了,内在的崩溃已经开始了。但它的凋谢却干脆利索,时候一到,花瓣们就一拍四散,落地成泥。并不像牡丹那样一团烂纸似的糊在枝上,不甘心又无能为力,真是不忍直视。郁金香的凋残就像一只精美的水晶杯子一样碎了,就什么都没了,剩下一排排秃茎,直愣愣地戳在哪里,好像还不明白自己头顶发生了什么的似的。没有一双眼睛会瞥它们一眼。 春天里应该去一次公园,和郁金香来个一年一会,这种和美的约会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美来搭救自己,正如迈克尔·波伦说的:“当盛开的鲜花那种非凡的美不再能穿透一个人头脑中的黑暗或者是固执想法时,这种头脑与这个世俗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危险地磨损了。”▲长按上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ujinxianga.com/yjxzp/5234.html
- 上一篇文章: 四月的花语是什么郁金香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